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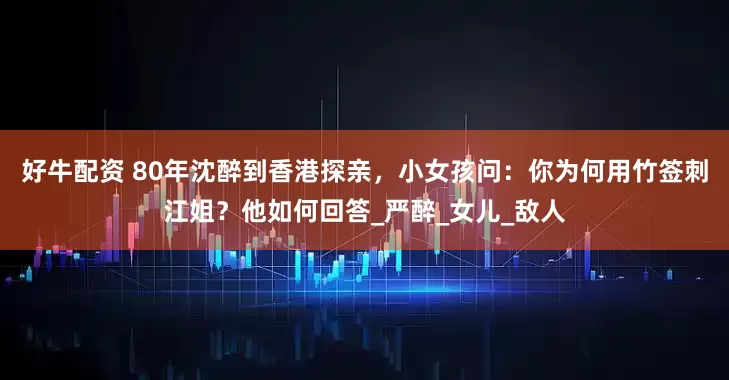
1961年年底,长篇小说《红岩》一经问世,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。
书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故事情节细腻且曲折动人,读者在阅读时常常情不自禁地代入其中,感同身受。
这部作品描绘了新中国革命战士们在国民党残酷迫害下,依然坚定不移地进行解放斗争的动人故事。书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:
主人公江姐被敌人捕获后,坚决不透露任何关于解放军的秘密。敌人对她的顽强抵抗束手无策,决定施以酷刑折磨。
在一个名叫“严醉”的人的建议下,敌人用十根锋利的竹签狠狠钉进了江姐的指甲缝里!
然而,这种令人锥心的剧痛不仅未能让江姐屈服,反而她坚毅地回应道:“竹签是竹子做的,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!”
江姐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让敌人无计可施,只能残忍地将她处死。因此,书中的“严醉”成为了人们痛恨的对象。现实中,“严醉”的原型是沈醉。
展开剩余91%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和改造后,沈醉已深刻悔过,每每回忆往事都感慨万千。
1980年冬天,在香港一间简朴的小旅馆门前,一辆出租车刚停稳,便有两名服务员热情地跑来,帮忙拉开车门,站在一旁等待乘客给小费。
车上下来的一老一少两人起初还没反应过来,老人微笑着和服务员握手说:“辛苦了,谢谢你们。”
服务员眨了眨眼,没有说话,见两人静静地站着不动,也不说话,老人突然像想起什么,掏出几张港币递给了他们作为小费。
这才换来了两名服务员灿烂的笑容和一句“谢谢”。
正在老人长舒一口气时,旁边年轻的女士笑道:“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吧?只有给钱了,他们才会道谢。”
由此可见,这对父女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而是来自大陆的旅客。
这就是66岁的沈醉和他的小女儿沈美娟,远渡重洋来到香港探亲时发生的温馨一幕。
沈醉生于1914年,儿时立志报国,但投奔亲人时误入歧途,成了军统局的一员。
孩提时代的他辨别是非能力有限,受到周围人有意拉拢与蒙骗,逐渐偏离了初心,最终沦为祸害一方的特务头目。
新中国成立后,沈醉在功德林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和思想教育。
在如春风般温暖的教化下,他痛改前非,从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转变为揭露国民党罪行的作家。
这次香港探亲正是他凭借改造表现争取来的机会。
第二天,沈醉的小女儿给母亲粟燕萍打电话,母女俩都急切想见面。
不久,粟燕萍和她的丈夫来接女儿,但沈醉本人并未出现。
他事先和女儿约定,不直接告知母亲自己来了,先让女儿探探口风,若母亲愿意见面,他再现身;若不愿,则不勉强,直接返回北京。
女儿“执行任务”期间,沈醉则与当年迁港的老友们会面。
久别重逢,大家话题不断。
不少朋友邀请他在香港长住,但沈醉坚持办完事就回北京,因为他心中认定那里才是自己的家。
一次,他的老友提议让沈醉见见自己孙女,沈醉欣然同意。
没想到,小女孩见到沈醉后怔怔地盯着他,陷入沉思。众人不解时,小女孩突然哭了起来,躲在爷爷身后。
在安抚中,小女孩半探出头,怯生生问:“你就是严醉吗?为什么用竹签刺江姐?”
这话让沈醉和周围老友皆无言以对。沈醉缓缓问她是否想听当年的真相,见小女孩点头,他便陷入回忆。
沈醉解释,江姐并未被竹签钉手。
当年,江姐被捕后,无论怎样审讯都不透露半点消息。
同事徐远举想出一个恶毒的主意,要剥光江姐衣服,以此羞辱她。
江姐毫不畏惧,义正言辞地说:“你们的母亲姐妹都是女人,你们这样的罪恶行为,终将被天下女性惩罚!”
江姐的正气让沈醉心生惭愧,他踢了徐远举一脚,暗示他另想办法。
于是,徐远举便用影视中常见的拶指刑——用绳子收紧夹住手指的小木棍,施以残酷折磨。
这种酷刑让人感受到骨头被碾压的疼痛,却又不至于断指,漫长的折磨令人难以忍受。
即便如此,江姐依旧坚强不屈,用钢铁般的意志维护共产主义事业,也在沈醉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文学创作为凸显江姐英雄形象,加强革命斗争的艰难,艺术化地将这段拶指刑改编为“扎竹签”的情节。
沈醉感慨万千:“江姐真让我汗颜,我过去确实罪恶累累,现在一定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!”
虽然江姐被扎竹签的故事是艺术加工,但沈醉对其他共产党员和无辜百姓的伤害是真实的。
那时,为完成军统任务,他曾跟踪、恐吓许多共产党员。
此外,为了确保中美合作项目按期完工,他还监督强拆一座煤矿及其周边民房,许多人无家可归,甚至有人死于凄风苦雨之中。
煤矿老板心血付之东流,没有军统补偿,选择上吊自杀。
沈醉虽怜悯这些受害者,内心也曾挣扎,但因沉迷于名利场,常以“身不由己”自我安慰。
沈醉曾有两段刻骨铭心的感情。
他的初恋白云,是厦门大学学生,受创办人陈嘉庚影响,胸怀报国之志。
白云和沈醉的信念截然不同。
军统头目戴笠察觉白云所在编辑部偏向共产党,暗中不看好二人。
他没有直接劝退,而是在沈醉试图说服白云时,建议先让她婚后安心做太太,不再与编辑部接触。
白云拒绝,随着时间推移,她越发认识到沈醉信仰与自己南辕北辙。
沈醉更像个资本家,无法理解工人辛劳及为共产主义奋斗者的伟大。
两人思想分歧导致痛苦分手。
后来,沈醉在临澧特训班工作时认识了粟燕萍。
她来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,性格坚毅活泼,总是面带微笑。
沈醉被她善良打动,不像白云有坚定信仰,很快产生感情。
粟燕萍比沈醉小六岁,未受系统教育,在沈醉温柔攻势下很快倾心。
因不喜欢干行动队工作,粟燕萍被调到通讯组,三个月后通讯组因火灾解散,她便投奔沈醉。
两人在常德举行婚礼,粟燕萍当时不到19岁,只想做个家庭主妇。
她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,为沈醉生了六个孩子,直到生出男孩才停。
解放前夕,为避免牵连家人,沈醉将粟燕萍和孩子送到香港。
当时台湾故意谣传沈醉等人已被处决,消息不明的粟燕萍伤心改嫁。
多年后,两岸开放探亲,沈醉在女儿鼓励下申请赴港,才有前述经历。
三天忐忑等待后,女儿带来好消息:“母亲和叔叔都想见您。”
重逢时,大家泪流满面,粟燕萍愧疚地说自己以为他已被处决才改嫁。
沈醉宽容理解,没有责怪,粟燕萍高兴地请求成为朋友。
沈醉笑着说:“什么朋友,你们是我的妹妹和妹夫。”此后众人释怀。
回忆这些岁月,沈醉感慨良多。
戴笠死后,作为军统头目的沈醉难逃制裁。
初入功德林时,他固执认为改造只是走形式,自己活不到出狱那天,对安排的活动极度抵触。
但时间长了,他发现没有遭到想象中的虐待,生活反而井然有序。
功德林管理严谨,尊重战犯人权,工作人员耐心细致。
春节时,监狱组织他们排练节目,甚至资助他们观看戏曲表演。
有次组织参观成渝铁路,国民党未能修好的铁路线,这次看到的是地道成都话的工作人员,让沈醉震惊。
他意识到共产党做事不同于国民党,不只是“面子工程”,深受触动,开始认真接受教育。
曾以为只是政治立场不同,做的事无伤大雅,现在明白共产党真正为人民谋福祉,国民党只是资本家的工具。
这让他深感羞愧。
1959年底,沈醉获特赦出狱。
因曾是特务头目,百姓仍有些畏惧。
他决心用行动证明改过自新,积极参与思想宣传,自愿为党服务。
文笔优良的他撰写了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、《保密局内幕》、《杨虎将军被害经过》等纪实文学。
作品揭露军统残暴,讲述自己亲历的事实,形成国民党腐败与共产党廉洁的鲜明对比。
不知此刻沈醉是否忆起了江姐。
谈及此事,他激
发布于:天津市恒汇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